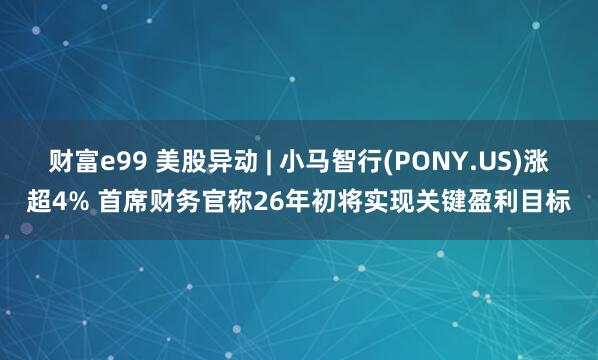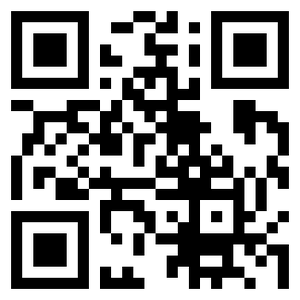前天是5月4日青年节,也是北京大学125周年的校庆日。庆典期间,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走上台,宣布将自己多年来获得的奖金和一部分个人积蓄捐出,总金额达一千万人民币,用于支持敦煌学的研究。这场捐赠仪式上金鼎配资 ,她说道:“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,所得的奖金要用于社会发展的事业。”从她的言语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与敦煌的深厚渊源。
这位老人名叫樊锦诗,她曾担任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,并被誉为“敦煌女儿”。她出生在上海,毕业于北京大学,在敦煌的土地上度过了半个世纪,将敦煌与自己的血脉紧密相连。事实上,我们今天能欣赏到敦煌的美丽和历史,离不开她的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。
01 ▼
展开剩余88%误打误撞,情深似海
1962年,樊锦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时,报名参加了敦煌研究院的实习。当时她对敦煌充满好奇与热爱,一到敦煌就迅速参观了一个又一个洞窟,内心深受震撼。但更让她震惊的,是那里的生活条件。她的宿舍是一间不到20平米的土屋,日常饮食极为简单,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。更糟糕的是,没有水电供应,更别提卫生设施了。
有一次,她半夜想上厕所,刚一出门就看到两只绿绿的大眼睛正死死盯着她。她吓得心跳加速,赶紧关上房门,惊恐地躺在床上等到天亮。第二天一早,她才敢再次出门。后来她才知道,那并不是狼,而是一头驴。
樊锦诗的父亲是工程师,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。她自小生活在优越的知识分子家庭,享受着丰盈的物质条件,从未经历过如此艰苦的环境。几个月下来,因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,她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。当时,她心里不禁想着:“我再也不想回来了!”
然而,命运的安排总是出乎意料。毕业分配工作时,敦煌研究院来北大招人,要求带走四个实习生。樊锦诗的父亲心疼女儿,特意写了一封长信,想劝她留在北京。然而,樊锦诗并没有将这封信交给学校领导,而是决定再次前往敦煌,走上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的道路。
一年后,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来敦煌看望她。他发现,曾经那位上海姑娘,变得更加沉稳,话语中带着大漠的沙砾与粗粝。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俏皮的都市女孩,而是一个深深扎根在敦煌的女人。
02 ▼
不称职的妻子与母亲
1967年,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,但由于工作上的分隔,两人开始了长达19年的异地生活。尽管北大的老师曾承诺会在三年后将她调到武汉大学与丈夫团聚,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这一承诺变得遥遥无期。期间,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。樊锦诗的工作异常繁忙,孩子们只能被她一个人留在宿舍,偶尔用绳子绑住,以防走失。每天当她下班回到宿舍,听见孩子的哭声,才松了一口气;若没有听见,心中便充满担忧。
她曾试图调到武汉大学,但一直未能如愿。直到1986年,领导终于同意调动她,然而她却犹豫了。这份对敦煌的深深热爱,已经融入了她的血液,改变了她的决定。她任性地对丈夫说:“反正我不走了,要不,你来吧!”
最终,彭金章先生决定追随妻子,扎根于荒漠,陪伴她共同度过了31年的岁月。他为中国留下了1600余年的文化遗产档案,成为了敦煌研究的重要支柱。多年后,樊锦诗在节目中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时,几度哽咽:“为了孩子,他不愿意来敦煌,但最终他还是理解了我,爱护了我。最后,我们终于团聚了。”
03 ▼
数字敦煌的伟大构想
1998年,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。在她的领导下,敦煌研究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她首度提出国际合作,利用现代技术进行洞窟环境监测,抵御沙漠的侵袭。此外,她还积极改善研究院的住宿条件,争取为年轻人争取出国进修的机会。
然而,她最值得称道的成就,还是数字化敦煌的建设。随着莫高窟对外开放,每年有数十万游客涌入,洞窟的承载力面临巨大压力。樊锦诗深知不让游客进入是不现实的,但也无法承受他们的破坏。为了更好地保护莫高窟,樊锦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——将莫高窟数字化,让游客在不进入洞窟的情况下,依然能够欣赏其美丽。
虽然当时的技术无法实现这个梦想,但她始终没有放弃。经过10年的努力,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终于建成,并推出了《千年莫高》和《梦幻佛宫》两部立体电影,利用虚拟技术将莫高窟的艺术魅力呈现给观众。这个项目不仅缓解了洞窟的压力,还为未来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
2016年,网站“数字敦煌”上线,全球的网民只需一部电脑,就能“亲临”敦煌,浏览30个经典洞窟和4430平方米的壁画。这些数字影像将成为敦煌文化传承的永久载体,延续着莫高窟的神秘与魅力。
04 ▼
坚守初心,淡泊名利
樊锦诗身上有着老一辈学者特有的学术气质。她不拘小节,对生活琐事毫不讲究,却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的执着。她的心中,只有两个字:“敦煌”。
2006年,第一卷考古报告完成,樊锦诗将初稿交给90岁高龄的宿白先生审阅。先生认为不合格,她毅然推翻重做,经过多次修改,六年后才正式出版。2009年,樊锦诗被评为“感动中国人物”,但她却表示自己不配这个荣誉。她不喜欢接受记者采访,常常谦虚地说:“我的故事很简单,不必写我,应该多写写敦煌。”
几年前,年近80的樊锦诗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,担任名誉院长和国务院参事。但即便退休,她的心依然牵挂着敦煌。她曾说:“如果没有敦煌,谁会知道我是谁?那不是我的荣誉,而是敦煌的荣誉。”
从25岁孤身前往敦煌,到84岁为敦煌捐出积蓄,樊锦诗的一生几乎与敦煌紧紧相连。她说:“我很普通”,但正是这个平凡又坚韧的老人,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对事业的执着与奉献,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传奇。
发布于:天津市牛道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